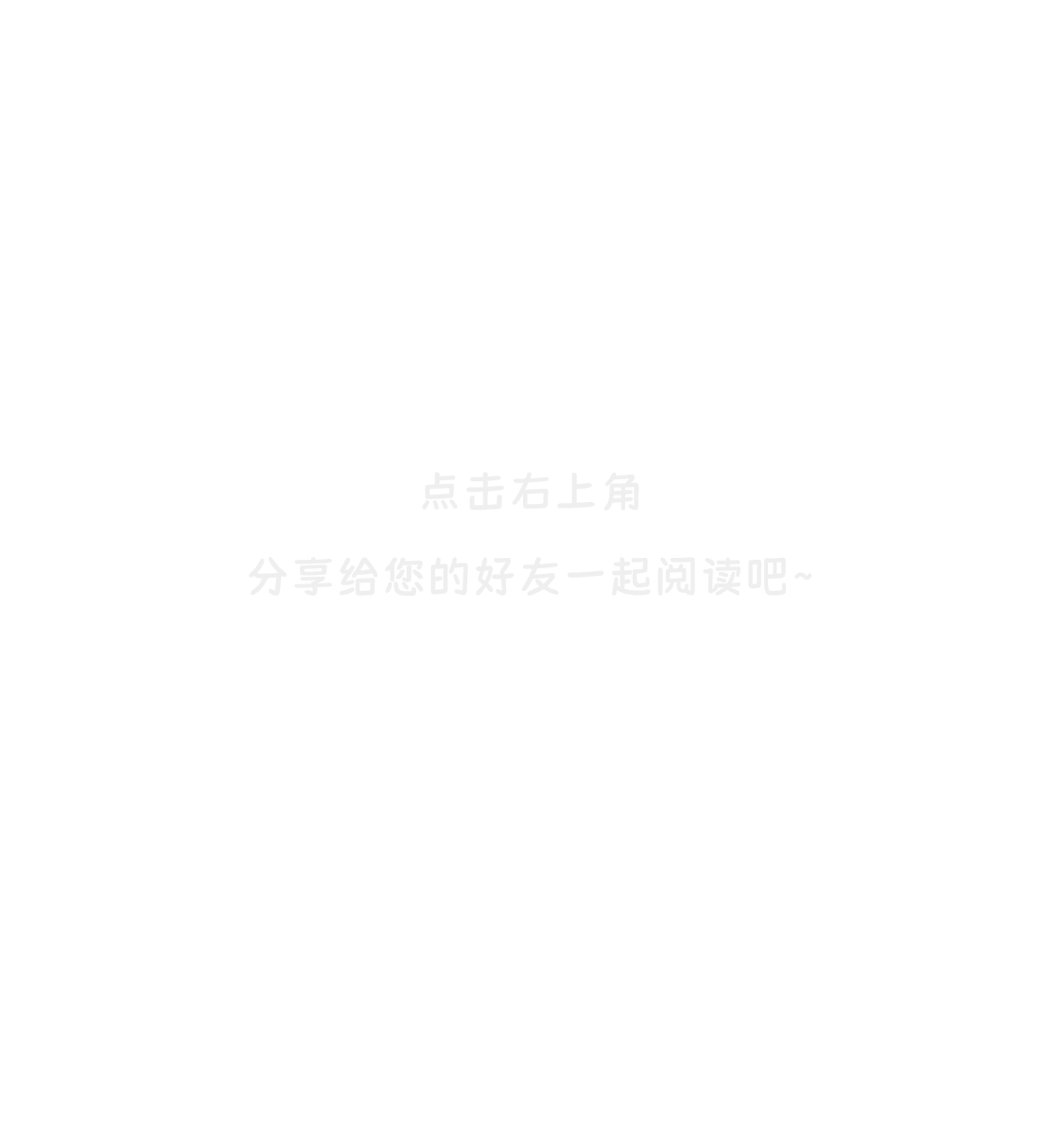文丨■周远德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海龙屯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堡之一。它作为中国土司遗址的代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活态标本,是军事史、制度史、民族融合史的交叉点,也是自然与人文共生的东方智慧结晶。

遵义中世纪军事城堡——海龙屯(胡志刚/摄)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活态见证
海龙屯并非孤立的山城,它是土司制度“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结晶,更是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场。
海龙屯的军事防御体系是古代山地筑城防御的智慧之作。海龙屯建在遵义龙岩山巅,又叫龙岩囤。龙岩山四面陡绝,地势险峻,只有山后一条窄径可以攀缘,易守难攻。始建于南宋末(1257年)的海龙屯,充分利用龙岩山独特的地形地势依山而建,最初是为了抵御蒙古大军而修建的军事要塞。其建筑设计精巧,各关隘均以巨石垒砌,并有城墙、瞭望台、石壕、箭楼等配套设施。
海龙屯的防御体系呈现出“关堡星布、以点控面、纵深防御”的特点。整个防御体系从外围到中心层层设防,构成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娄山关、三渡关、上渡关等组成,主要作为警戒阵地;第二道防线由养马城、养鸡城、海云屯等组成,主要作为火炮阵地;第三道防线由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等组成,是主力决战场,也是最后一道屏障。其中,飞虎关的三十六步天梯,全长52米,宽4.15米,呈30º的坡形,每级台阶高约0.5米,进深1米多,需手脚并用攀爬。这3道防线层层耗歼,逐次阻敌,构成了长达60余公里的纵深防御阵地。
海龙屯虽然在宋蒙战争中并未真正成为战场,但其军事防御功能的设计,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中,成为播州杨氏土司杨应龙与中央王朝军事对抗的最后防线。海龙屯不仅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建筑风格融合了汉文化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杨氏土司统治时期,播州苗族、仡佬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自杨端入播以来,大力推行汉文化,以孔儒思想教化人民,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在杨汉英统治时期(元朝初年),播州地区的教育呈现出制度化、儒学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体现出明显的“汉化”与“地方治理”双重功能。“急教化,大治泮宫”,杨汉英积极修建文庙、儒学和书院,推动儒学教育在播州制度化落地。他还上书请求设学开科,使播州教育从“养士”走向“选士”,与国家制度接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播州宣慰使司派遣子弟到京师求学,学习中原文化,接受儒学文化的熏陶。同时,还在播州设宣慰司学,除招收土司子弟外,还允许部分民间子弟入学,播州“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逐渐“世转为华俗,渐渍于礼”。他不仅推动儒学教育,更以理学教化地方,强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促进了民族融合。教育成为播州从“蛮夷之地”向“礼乐之邦”转型的关键力量。
自然与人文共生。海龙屯作为贵州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土司制度的历史见证,更是自然与人文共生共融的典范。一是以山水为骨,自然地形塑造人文格局。海龙屯选址“依山为屏,借水为险”,三面环溪,一径通幽,九道关隘沿山势蜿蜒而上,形成“山即是城,城即是山”的防御体系。二是以文化为魂,历史记忆嵌入自然场域。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共生,城墙、宫址、水牢等遗存与杨氏土司家族记忆、仡佬族传说、军事战争叙事共同构成“活的文化地层”。三十六步天梯、飞虎关等节点不仅是军事设施,更是土司权威的仪式化表达。行走其间,石阶的压迫感与山体的巍峨形成“人在自然中感悟权力秩序”的精神体验,形成仪式化空间的自然共鸣。三是以生活为韵,现代转化中延续共生智慧。如今的海龙屯通过数字音景还原古战场回声,非遗工坊将拓片、酱酒酿造等传统技艺嵌入旅游动线,游客“白天访遗址,夜宿观星空”,形成“自然—历史—生活”的时空连续体。四是以精神共鸣,从地方经验到文化价值。通过“保护—阐释—体验”,海龙屯将生态保护要求转化为文化吸引力,通过自然与人文的有机融合,实现“保护遗产即保护山水”的现代共识,是可持续旅游的共生范式。这种“山—城—人”三位一体的格局,不仅展现了海龙屯的独特性,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东方智慧。

海龙屯(杨舰/摄)
土司学的“百科全书”与边疆治理的活态标本
作为中国土司遗产的典型代表,它既似一部“百科全书”,又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物化表达”。
制度史价值:海龙屯的制度史价值,集中体现在它是中国土司制度从兴起到终结全过程的“制度标本”,并以其遗址群、文献与考古成果,为研究“国家—地方”关系提供了连续时空样本。一是海龙屯遗址见证了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三种治理模式的交替,时间跨度长达344年。二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互动的“制度实验室”。屯内出土“示禁碑”“赏赐碑”等碑刻,记录了中央对土司的授权、惩戒与赏赐;战后海龙屯被毁、播州改流,标志中央重新确立直接治理。三是“因俗而治”治理智慧的实体案例。海龙屯的布局兼具军事(关隘、屯堡)、行政(衙署)、祭祀(家庙、玉皇阁)功能,体现了“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治理思想;遗址中出土的景德镇瓷器与地方陶器并存,反映土司政权在物质文化上“既连中央又接地气”的双重角色。四是土司制度下“世袭政治”的微观标本。杨氏27代30世725年连续统治,其世袭合法性通过海龙屯的宫殿规模、墓葬形制(如杨粲墓)不断强化。考古发现的新王宫、校场坝、仓储区等,揭示了杨氏土司如何以家族为核心,运转行政、军事、司法等公共职能,成为研究“世袭官僚制”的实体模型。
军事史价值:海龙屯的军事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城堡”本身,更在于它完整承载了宋、元、明三朝西南边疆战争的攻防逻辑与制度变迁,是研究中国古代山地军事防御体系的“活教材”。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从“抗蒙山城”到“反明堡垒”,实现战争功能的历史转型。1257年,杨氏土司奉南宋朝廷之命修建海龙屯,作为抵御蒙古南下的一道屏障。万历年间,杨应龙将其扩建为对抗明军的最后据点,屯内新王宫、校场、粮仓、军火库等设施齐备,成为地方政权挑战中央的军事中枢。二是成为“平播之役”主战场。明廷调集8省24万兵力,分八路围攻,耗时114天,耗费白银147万两,伤亡4万余人。明军使用云梯、火炮、挖掘地道等多种战术,守军依托天梯、飞虎关等险隘层层阻击,以滚石、火攻反击,最终杨应龙自缢、焚宫,城堡陷落,土司政权覆灭。海龙屯是研究明代大军团山地作战、攻防转换的实战样本。三是军事组织与后勤制度的实证材料。杨氏长期实行“兵农合一”制度,海龙屯周边分布大量“屯”“堡”“哨”遗址,体现土司自营的军事屯田体系。考古发现大型粮仓、兵器库、马厩、水井,说明其具备在长期围困下的自给能力。出土明代边军棉甲片、马骨、火铳残件,反映当时南兵北调、火器使用与骑兵配置等军事细节。

海龙屯(胡志刚/摄)
多学科交叉价值:海龙屯不仅是“土司制度”的物化样本,更是一座天然的“多学科交叉实验场”。十年间,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催生了“土司学”研究热潮,出版《海龙囤》考古报告等专著20余部,填补了土司研究多项空白。一是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制度的时空坐标。通过地层与碳十四测年将南宋抗蒙山城—元明土司城—明末战争遗址的演变锁定到30~50年精度,为宋、元、明三代西南边疆史提供可复核的“硬时间轴”。出土碑刻、印章、瓷器题铭与《明实录》《播州宣慰司志》等文献互相印证,首次把“土司承袭—朝贡—改流”三大环节的原始凭证链拼合完整。二是建筑学—军事工程—GIS空间分析:山地防御的“算法模型”。利用无人机航测+三维激光扫描,建立毫米级地形模型,揭示9关3线防御体系如何以最小石材消耗换取最大拦截面(土方量/拦截面比1:12,同期北方长城为1:5)。天梯段36°—42°的踏步角度,经步态实验验证恰好是披甲士兵极限攀爬角,为冷兵器时代军事工程的人体工学设计提供样本。三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土司社会的“全息剖面”。DNA同位素分析显示,海龙屯与杨氏土司墓地人骨中北方草原成分随时间递减,而与苗瑶语族人口相似成分递增,直观反映700年间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与人口流动的社会学曲线。四是环境考古—农业史—动物考古:山地经济的微缩景观。浮选出的水稻、苦荞、高粱碳化种子比例,结合孢粉数据,复原出明代播州“双季稻+高山杂粮”垂直农业带,解释了海龙屯被围114天而粮不绝的生态基础。通过马骨DNA比对证实,屯内战马与滇马、蒙古马存在杂交谱系,为西南山地骑兵战术与茶马贸易提供动物考古学证据。五是文化遗产科学—数字化—传播学:活态利用的“海龙屯模式”。构建“学术—科普—青少年”三位一体的传播体系。225万字《海龙囤》考古报告入选“2022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AR技术还原的“平播之役”互动地图,以游戏形式吸引公众参与;同时,与地方党校、中小学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年接待研学学生超12万人次,推动文化遗产“活”起来。当地村民转型为“文保员+非遗讲解员”,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KPI”直接挂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社区驱动型遗产管理”案例。六是艺术史—影像人类学—创意产业:跨媒介叙事实验。2024年第二届海龙屯国际影像周,无人机灯光秀把海龙屯9关防御体系“投射”夜空,打造沉浸式剧场。如今,海龙屯故事已孵化纪录片3部、网络小说2部、动漫1部,形成“土司IP”雏形,带动周边文创产值年均30%增长。
海龙屯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城堡”本身,更在于它浓缩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自然与人文共生的生态哲学,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